[个人简介]
章百家,1948年1月生,中共党员。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硕士学位,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外关系第一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现任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章百家先生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外交史和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期刊和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和参与了多部学术著作的编写,主要代表作有《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冷战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国共产党三部曲》《腾飞之道: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史》等。

[以下为校友访谈内容]
1.通过对您求学经历的了解,我们注意到您是恢复高考之后考取了北京大学,后来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我们想知道,当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哪些方面比较吸引您?
我是所谓的“老三届”,我们这些人的求学经历比较曲折。“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上高二,后来又插队、当兵。1978年,我是穿着军装参加高考的。我原想考经济系,觉得现代化建设最需要的是这方面的人才。但那时部队有规定,考大学文科只能选中文、哲学、历史这三个专业,于是我就考了历史系。这个选择并非一时兴起。我对历史产生兴趣并开始自学是在“文革”后期,那时思想上的困惑很多,我觉得学历史或许是解疑释惑的最好办法。考入北大后,我学的是世界史专业,主修美国史,授课老师有罗荣渠、齐文颖等名家。本科四年,我受到系统的史学训练、开阔了眼界,也初步确定以研究中美关系史为努力方向。当时能找到的书全部是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写中国对美政策的书连一本都看不到。我感到,中国人更需要了解中国的事,这是日后我改学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学毕业后,我按照当时军队学员“哪儿来哪儿去”的规定,返回原单位工作一年。1983年,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近代史系民国史专业。这一年正赶上军队大裁军,我考上研究生后就从部队转业了。
2.您在研究生院求学时,研究生院是怎样培养学生的?这段求学经历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哪些方面?
我进研究生院时,学校仍在初创阶段,没有自己的校舍,专业课由各所负责。我在近代史所度过了最为难忘的一段求学岁月。回想起来,近代史所有三大优势:第一是名师云集,有许多学识渊博、阅历丰富的老先生,也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中年学者。我的两位导师,李新先生属于前者,李宗一先生属于后者。我进所后一个突出感受是前辈对晚辈的关爱。许多老先生待人平等,乐于同年轻人聊天,有问必答,融教诲于探讨之中。第二是学术空气浓厚,治学严谨,思想开放。近代史所严谨的学风始自创建者范文澜先生,并得到很好的传承。而思想的开放则突出表现在求真求实,勇于打破禁锢,探讨各种新问题。我的导师李新先生就堪称这方面的表率。他是一位老革命,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他思想开明尖锐,很有见的。第三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条件一流。所图书馆馆藏近代史档案资料无论在国际国内都首屈一指。对于研究生的学习,所里比较放手。导师上课多为探讨式的,主要是要求学生多看书,尤其是多看史料,大胆钻研。不过,到毕业论文写作阶段,各项要求很严格,毫不含糊。在我看来,环境的熏陶特别重要。近代史所的风气对年轻人求学非常有利,口传心授更能让学生体验到前辈的治学态度与方法。

3.您从世界史跨到中国史,从民国史转向中共党史,后来又从事改革开放史研究。请问您是怎么处理史学研究专与博的关系的?
我个人的研究主要还在外交史方面。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各领域各专题总有相通之处。专与博是相对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就我自己的体会,一个学者的成长,个人兴趣和努力固然重要,机遇也很重要。我们这一代学者是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我的研究方向前后有所变化多因工作转换,而不单是个人选择。
1986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了十年。这段时间有两件事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很大。第一件事是1986年秋参加中美双方联合举办的中美关系史研讨会。这是中美两国学者第一次坐在一起进行讨论,涉及的1945年至1955年的历史当时还很敏感。这次会议经过为期一年的精心准备。会议的安排很有意思,设9个题目,双方各提交一篇论文,撰写者都是40岁上下的中青年学者,双方的顾问团队则由资深外交官和著名学者组成,负责点评。参加这次会议令我大开眼界,知道了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标杆应定在哪里。我提交的论文和所写的会议述评随后在《历史研究》发表,同期杂志刊登一位作者的两篇文章算是破例。会后,我被选派参加中国社科院和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组织的高级学者互访项目,获得了直接观察和了解美国的机会。那时,我还没评学术职称,连实习研究员都不是。回想起来,那真是用人不拘一格。
另一件事是上世纪90年代初参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编写工作。我被推荐参加这项工作的原因是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涉及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同苏联和美国的关系。编写这本书的流程大致是先由胡乔木先生的口述,我们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查找档案,编写初稿;然后经他审阅,提出意见,再加以修改。在编写过程中,乔木先生反复强调的是要把历史事实和过程写准确、写清楚,少发议论,如何评价是后人的事。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本书由于乔木先生去世未能完稿,最终以“谈话录”+“初拟稿”的形式出版的。参加这项工作使我有机会得到胡乔木、胡绳、龚育之等大家名师的指导;同时,通过查阅大量的档案也使我对党的历史有了很多实际感受。
4.在学术研究方面,您最看重研究生哪方面的长处?您对当前中国的研究生培养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以历史学研究生的培养为例,在我看来,一名优秀的研究生首先要对历史有兴趣,而且这种兴趣要超过对其他问题的兴趣。做历史研究,既要沉得下心来,又要思想活跃。一般来说,坐得住冷板凳的往往思想不很活跃,而思想活跃的往往又坐不住冷板凳。如果二者兼备,那就有成为一名出色历史学家的潜质。
我喜欢能同老师讨论问题的学生。从事研究性工作,一定要善于提出问题,有批判眼光。不能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师带学生的过程不是学生单方面受益,老师也会从中受益。最好的师生关系一定是双向互动。例如,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是选题要具有开拓性。这意味着对导师来说这也是个新题目。学生要写出一篇具有开拓性的论文,就必须做相关的学术梳理,掌握更多史料,找到新视角,提出新观点。这样,导师指导学生的过程必然是教学相长。
5.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成立,您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建议?您对学弟学妹们有什么话想说?
我以为,品德教育和人格教育是大学教育很重要的内容,而其中一点就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意识和能力。“学以致用”是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但对“用”字的理解不能简单化,对基础性学科来说更是如此。同学们学习历史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把历史放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去理解;二是与现实进行比照,找寻与历史之间的异同。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可以提供借鉴、提供启示,但通常不能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只有在历史与现实中巡游探索,才有助于“追求真理”这个永恒主题的实现。
最后,祝愿母校越办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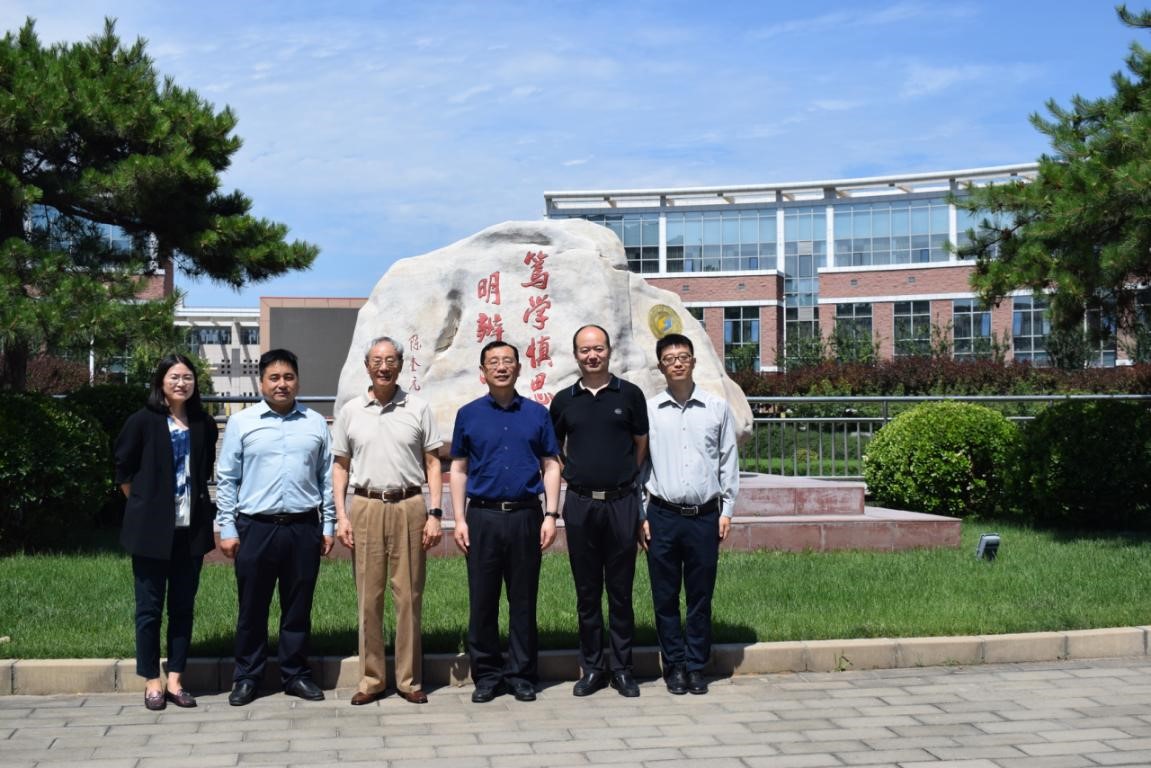
采访:王凯、李奎原
撰稿:王凯
审校:闫雷、刘强、魏万磊
